伦敦——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曾写道,文学奖项“如果你得了也没有关系”。中国的当权者们对待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远没有这样从容。
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融入国际社会,自那时起,中国政府一直渴望诺贝尔文学奖能授予一名在中国生活、工作和取得成功的中国公民,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世界上的现代强国的证明。中国对诺贝尔奖长期以来的羡慕,使该奖变为集体功劳的象征,而不是个人创造力的象征。
理论上来讲,诺贝尔文学奖在周四颁发给莫言应该可以终止中国的诺贝尔情结了。莫言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官方组织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欢欣鼓舞的中国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和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即刻向莫言表示祝贺。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断其正常节目,插播莫言获奖的特别消息。
和之前的中国血统诺奖得主所引发的反响相比,这次有显著不同。流亡海外的作家高行健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北京谴责诺贝尔委员会(Nobel Committee)出于“政治目的”颁奖。当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异见人士刘晓波,中国外交部把诺贝尔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描绘为对该奖的“亵渎”。刘晓波因为从事支持民主的活动被判刑11年,至今仍被监禁。
然而,尽管官方为此欢呼,莫言获奖也引发了政治争议。中国异见人士对此表示不满,用艾未未的话说,莫言获奖是对“人性和文学的侮辱”,因为莫言向政治体制妥协,并在刘晓波受监禁一事上保持沉默。批评家还提及,莫言在今年早些时候和其他作家一起抄写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方针的原始文本——以作为《讲话》的特别纪念版。一名愤怒的网民则直接在网上发布了自己对着莫言照片竖中指的图片。
莫言的中国攻击者(那些生活在专制审查的日常现实中的人)有理由作出批判。近年来,莫言一直在设法躲避政治争议。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Frankfurt Book Fair)上,中国成为“市场焦点”,出任中国官方代表团文学代表的莫言则容忍自己发表乏味的演讲。和代表团里的其他人一起,他尽职尽责地抵制了有流亡中国作家参与的活动。出席今年4月举行的伦敦书展(London Book Fair)时,他同样地照本宣科。据传言,中国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都收到一个长长的单子,上面列出不能和外国媒体讨论的禁忌话题——最为突出的是对薄熙来的整肃,薄家的丑闻正是在书展期间爆发的。
然而,如果在远处观望这些争议的西方人,把莫言看做文学傀儡而认为他不值得一提,或认为他所著的几本有关1949年后的中国的历史小说只呈现一个经过官方过滤的中国及其近况,那是他们不肯动脑子。自从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出版《天堂蒜苔之歌》以来,莫言的小说一直寻求暴露共产党统治下盛行的残暴、贪婪和腐败。
例如,以虚构的、与书名相同的中国省份为背景的《酒国》(1992年出版)一书,是对中国新兴市场经济的精神空虚的辛辣讽刺。莫言的小说可能写作技巧不够完美,也没有向当代中国最敏感的禁区开刀,包括1989年对民主抗议活动的镇压,或中共领导人及体制对中国很多政治不平等现象应担负的责任。但他叙述的怪异场景所表达的,是对人民共和国的尖刻洞察,而且,通过合乎逻辑的延伸,也是对该体制设计者的尖刻洞察。尽管他对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现状很少直接批判,但他作品的评判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在理解莫言本人及其小说关于今日中国告诉了我们什么,而不是谴责莫言在政治上的妥协。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该体制的懦弱让步者和英勇抵抗的异见者之间的善恶之争(尽管中国不缺勇气非凡、敢于向权威说真话的个人),而是一个各种声音都力争在政治允许的范畴里生存的现实,这个范畴有时意外地大;一些作家(包括莫言在内)不时外推其边缘。
莫言在获奖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回应批评者时,也间接提到了这一模棱两可的现实:“很多在网上批评我的人,他们本身也是共产党员,他们本身也在体制内工作,有的人甚至在体制内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如果他们看过我的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
莫言是一个一面和当局者公开游戏、一面为自己保留了创作空间的作家,这使他能够向同一当局提出间接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对莫言的攻击似乎打破了他对政治的惯有沉默。获奖之后,莫言曾公开表示自己希望刘晓波“能尽快获得自由”。
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许预示着其得主将迎来更有意思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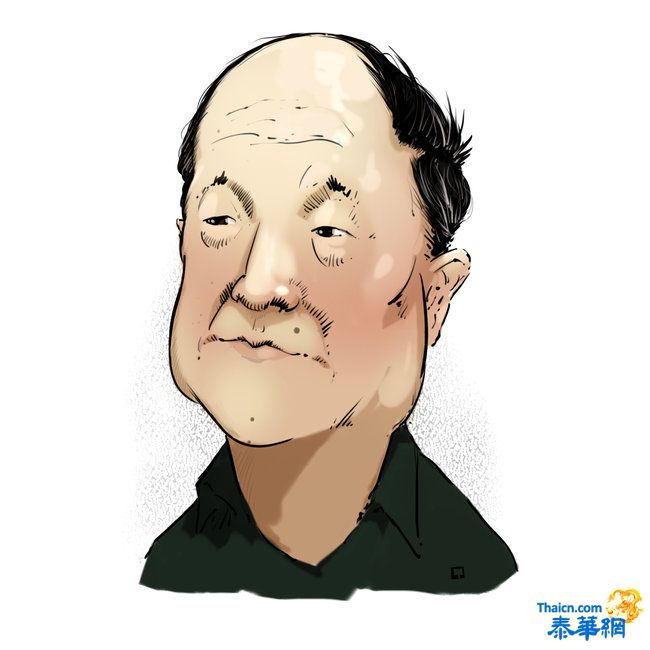
ㄥㄥ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综合资讯 » 纽约时报:莫言笔下的中国
